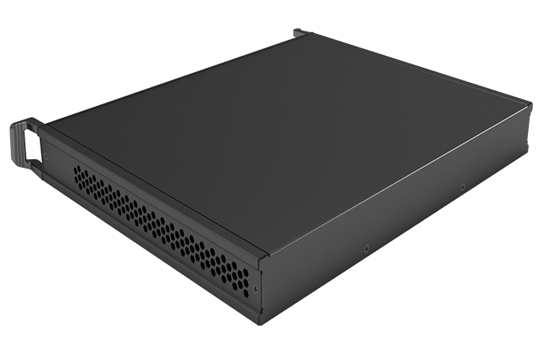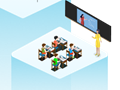無論何時,讀寫都須凸顯母語屬性
http://m.prostar-power.com2025年06月25日 10:32教育裝備網
在今天這個AI(人工智能)時代,談論國民閱讀寫作應當凸顯母語屬性,是否贅余?是否煞風景?是否杞人憂天?
1912年,蔡元培先生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,頒布“大學令”廢除經學。蔡先生學問兼容中西,是清朝翰林出身,傳統文化根基深厚,他此舉并非要把經學從教育中剔除出去,而是把經學從學子的“信仰”系統變為研究對象,在此后的教育現代化進程中,如將《詩經》納入“文學”,《春秋》納入“史學”,《易經》納入“哲學”等,逐步變身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范疇和分支。然而作為學術研究之外的國民閱讀寫作,如何和擴大化的傳統文化完美對接,這在新文化運動之后,成了一個一直在實踐之中而缺少完美答案的命題。
新文化運動之后,白話文逐漸成為國民書面表達的主流語體,隨著時間推移,更是成為國民閱讀的主流語體,久而久之,文言文非但從表達主流中退出,而且因降低了日常閱讀而逐漸變成了中小學生口中的“三怕”。語言不僅是思想的載體,也因之而影響對其內質的日漸疏離而浮于表象,成了孤零零的沒有根性、缺少魂魄的蟬蛻。
魯迅、胡適反對的傳統包括文言文中的糟粕,然而他們絕非要割裂與傳統文化的聯系,又焉能割得斷,他們排解其中毒素,謀求建設理想的語體、文脈、文氣、精神,而且摒除教條的、機械的、浮夸的、虛偽的風氣與思潮。就深層次論,我們謀求建構的母語閱讀與寫作的底線和基礎無外乎以此為根脈。哲學家羅素1920年在北京講學,曾批評中國文化的一些壞傳統,也毫無保留地贊揚中國文化,對當時部分知識分子不加選擇地反對本國傳統不以為然。思辨的、實證的、求真的方式與氣質對我們當下的母語讀寫而言同樣不可或缺。一百年來,我們的母語讀寫都需要找到一個科學、理性對接古今、中西的“度”,這應該成為一種日常的文化自覺。
相對于百年前母語源于文化驅動的自我更新,面對AI時代人工智能的強力沖擊,母語讀寫的改變,從內質到形式差不多處于一種沉浸式被動改變的狀態。近年來,從外來的Grok3、ChatGPT,到國內的DeepSeek,帶來的變化日新月異,令人目不暇給。無論是專業工作者,還是我這樣的外行,都很難置身事外,很多情況下是被卷入其中的,部分判斷是非智性、無邏輯的,而且未來還有更大的不確定性。
比如有的作家因為AI具有“強大”的寫作能力而擱筆,其實這并不能代表人工智能的強大,而很可能是作家自身的問題,是思維或者寫作能力的衰退。而且,國民寫作能力的高低以作家尤其以小說家為尺度進行考量并不合適,當代小說家更注重敘述方式或者想象能力,大部分是“文人”而非“文化人”;而且學力也與學歷無關,如沈從文幾乎沒有受過正規教育,但是他對古代服飾研究、文物研究包括其書法都獨成一家,小說之外的散文創作同樣蘊含獨有的母語特質。有的評論家說起人工智能所寫的舊體詩詞超過了時下95%的人類創作,這其實也并不顯見人工智能的水平高,而是襯托了目前母語傳統文體寫作的水平之低。筆者請DeepSeek寫一首關于濟南曲水亭街的七律,回復如下:
青磚碎瓦映清泉,垂柳依依繞曲川。
兩道小橋連古巷,幾株綠樹掩亭軒。
浣衣聲里尋幽夢,簪影燈中憶舊年。
流水潺潺千載韻,家家戶戶話詩篇。
呈給著名學者孫紹振閱讀,孫老覺得末句有點兒煞風景,反饋之后DeepSeek修改為“一街風月入詩箋”,改過之后中規中矩,有點兒像流行歌曲被捧成神話的中國風歌詞,因為是大平臺而缺少針對性,不太貼切。如果和它“開玩笑”,譬如請它填一首關于“赤壁”的詞,詞牌《念奴嬌》,它就會改“大江東去”為“長江浩渺”,換“故壘西邊”作“赤壁磯頭”,其他則照搬蘇學士的原詞奉上,大約“千古絕唱”不適合改來改去。無論如何,在許多人眼中,人工智能已經近乎無所不能了,不過對進行母語閱讀寫作而言,有許多事它仍舊無法替代人類——然而于此,人類又將何為?
我們仍舊要堅持進行真實的經典閱讀,進行真實的母語寫作。在閱讀過程中,首先要注重質量,其次要達到一定的數量。古人最知名的啟蒙詩文讀本是《唐詩三百首》和《古文觀止》,選錄作品是否全部經典見仁見智,但是編選者是奔著“觀止”來選的;《紅樓夢》中林黛玉教香菱學詩,選李白的七絕、王維的五律、杜甫的七律做范本,林黛玉的眼光無疑極高。唯有讀一流作品,才有可能養成一等眼光和一流素養,總是閱讀“爽文”,必然寫出“薛蟠體”。讀懂唐詩起步需“三百首”,觀止古文數量是220篇,“黛玉老師”規定的篇數是各詩體分別一二百首,閱讀精品積累到一定數量,文氣、文脈、遣詞、造句、布局、謀篇自然涵養而成,凡事問“智能”,素養哪里來?
我們仍然要珍惜真實的閱讀體驗,獨一無二、充滿特質的閱讀體驗,唯有如此,大千世界才可以林林總總,目之所及方可以琳瑯滿目,每一朵春花、每一聲夏雷、每一枚秋葉、每一片冬雪才會多姿多彩,絕不復制他者與自我。每一次心跳都有自己的溫度、自己的節奏,每一聲吶喊都擁有自己的分貝、自己的調性,每一滴眼淚都將可能孕育一場關于悲憫的泠然春雨。
我們仍然要葆有真實真切的閱讀認知,仍然要抒發獨一無二的探索感受,不被他者灌輸,不替機器代言,盡管它可能會無所不能,然而我們仍然高貴為宇宙精華、萬物靈長,我們要呵護自己的大腦,守望自己的心靈。
劉慈欣坦言,生活在科技的安樂窩中,人工智能毫無惡意地按照人類意愿行事,人類自己的開拓精神卻會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消弭。有網友拿他的科技背景說事,殊不知這并不是一個科技話題,這仍然是一個古老而嶄新的哲學命題。科技與科學并非一體,科技可以勢利眼似的鄙視人文,而科學一直與人文同在,一體兩翼守護著人類的尊嚴、智商、情懷和深度。所以,把AI做你善意的助手和伙伴,繼續你具有挑戰性的母語閱讀寫作之旅吧,它永無止境。
(作者系濟南外國語學校特級教師、中國教育報2020年度推動讀書十大人物)
責任編輯:董曉娟
本文鏈接:TOP↑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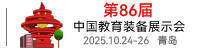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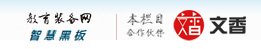

 首頁
首頁